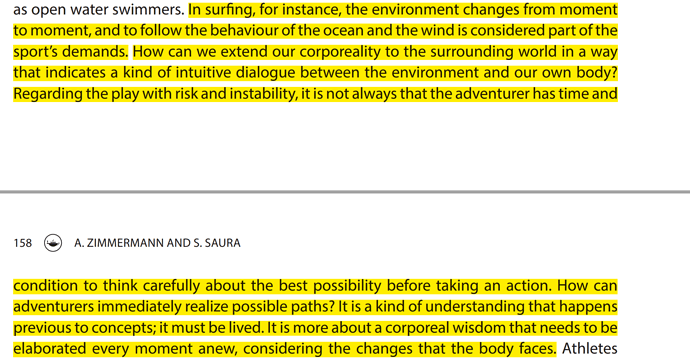首先,我觉得现实世界和虚构世界都值得我追求,没有“更值得”这一说法。
我认为可以称作经历。就像主楼里说得,想象出来的东西也会变成我们的记忆,他们和现实中的经历一样,会成为影响甚至塑造我们的东西。不然我们在学习时的思考算什么?
通过想象构造的事件,和现实世界中的经历不同之处在于,如果你没有在现实世界中经历过,那你就无法想象。举个例子,你无法向一位先天盲人解释什么是红色,如果你没品尝过什么是甜味,那你也无法想象一块草莓蛋糕有多么香甜。因此,想象其实是现实经历的一个延伸,或者说想象还是基于现实经历的。
感觉现实经历更真实是因为我们有感官。现实中,我们的经历还由五感组成。我们可以用眼睛观察一个东西,也可以用鼻子闻它的气味,如果它能发出声音,还会被我们的耳朵接收到,甚至某些情况下,我们可以直接用嘴尝它的味道(神农尝百草:D)。这种多感官的刺激,会直接把这些数据传送给我们的大脑。而想象可能只有大脑一个人在“孤军奋战”,想象反馈给大脑的数据还不够多,起码没有现实中用五感来的多。因此可能会产生现实经历比虚构经历更真实的直觉。
我觉得真这样做到了,可能会有点危险哈。根据2.1,这相当于你在虚构世界(或者想象)中产生的“数据”,或者说对大脑的“刺激”,已经等于甚至超过现实中各种感官的总和了。这样或许会导致人们无法有效区分现实和虚构,因为他们似乎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了。所以,或许只有那些因为这个原因,而待在精神院的人,最了解具体情况吧。
命题F下面的问题:
我认为或许不只有命题G里面提到的,想象越详细,越有机会取代现实记忆。F中提到的宗教信徒可能是那些“狂热”崇拜者。他们信奉的宗教很可能把他们从现实中的一些事“解脱”了出来。就像溺水的抓住一根稻草不放一样,宗教,或者所谓的“神迹”是他们最后的希望,哪怕这个希望很渺茫,甚至不存在,他们也会坚信看见了“神迹”。这其实像是“自己说服自己”,“自己欺骗自己”,并非一定是想象干预了记忆。不过命题F中,“感官数据会被写入记忆中,这是不受想象影响的。” 这也不总是对的。就像后面提到,庭审时出现记忆错乱。如果我们的记忆不再清晰,也就意味着能刺激我们大脑的五感减少了,那这个时候,想象能带给大脑的刺激就会大于,甚至远远大于现实记忆。因此这种情况下,我们会倾向于用自己“合理的想象”来替代之前模糊的现实记忆。
这个我认为可以分类讨论:1. 当想象的场景很短(想象持续时间不长)时,一个想象力非常强的人,是很有可能自由将想象世界当作自己真实的记忆。
2. 当想象持续得很久的时候,我们的肉体还是会因为时间的流失而产生反应,这或许会导致身体(现实肉体)和大脑(想象)接收的信息不一样,从而让想象的东西无法像真实的记忆那样符合现实的逻辑。比如,你很饿,然后坐在椅子上想象你吃一顿大餐,吃了一个小时,结束后你起来,还是会感觉饥肠辘辘,甚至有可能还会觉得腰酸背痛,因为你坐着不动太久了。这就是你在“想象”时,现实世界对你造成的影响。
3. 还有一种情况,就是在想象结束后,过了很久,久到你对那时现实状态的记忆都模糊了,那么你想象出来的东西就可能会取代真实的记忆。原因就是之前F里回复的,想象对大脑的刺激>现实对大脑的刺激。
现实是我们能通过五感察觉到的,而虚构则不能。比如,你无法通过观察,知道一个人此时此刻大脑中在想些什么,但你可以通过“虚构世界”中,大脑的推理或猜测,来想象出那人在想啥。所以现实世界只能带来客观的东西,而虚构世界在现实世界的基础上,添加了主观的思想。这也是它们之间的差异。
命题H我也同意,他们是现实世界的产物。
因为自我实现和尊重需求是人们的主观意识,属于虚构世界,并且是因人而异的。那些没有人类进化得复杂的生物,就不会有这种需求,因为他们更加关注于现实世界,却没有那么复杂的虚构(或者精神)世界。它们之所以“在想象中和现实中并没有区别”,是因为现实世界的一部分是虚构世界的折射。
一件事情越接近本我,它在现实中的占比越大。反之,它越接近超我时,就会越接近虚构世界。在这句话的理解中,现实是指:自然发生的事物,和生物的本能反应。这是狭义的”现实“,但其实广义的“现实”是会受到虚构世界的影响的,它是狭义”现实“和虚构世界的共同体和混合体。就像我们的某些行动并不是我们的本能(本我),但是在经过虚构世界(超我)的思考后,我们做出或许将会违背本能的行动,而这个行动就是自我,它像广义现实一样,收到本我和超我两面的影响。
想象食物有多么美味,更加接近超我的概念(虚构世界)。命题H里说得,是“基本的生理欲望”,是能不能吃饱,会不会吃死的问题(更接近本我),而不是更加“高级”的,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吃。因此并不会和命题H矛盾。
认同命题D。问题4中,“我们不再拥有一个客观的历史可以相互验证”,并不会,既然脑机接口中的“类似的现实世界”(或者就叫虚构世界吧),很难在真的“现实”(本我)中验证,那么就在虚构世界(超我)中验证。总的来说,如果命题D中的“现实世界”是广义的现实世界(及 狭义现实和虚构的混合体,或者在命题I中理解为的“自我”),那么命题D仍然正确。我们比如脑机接口中,连接大脑的机器,肯定会保留我们在它创造出来的世界里的“痕迹”和数据,那么以后的人们,就可以用这些数据来作为验证这段历史的证据。
类似,但不完全相同。想象世界纯纯靠大脑构造,而“脑机接口所提供的‘现实世界’ ”是用机械来辅助我们的想象,甚至可以通过刺激我们的五感,来无限模拟出真实世界里的感受。但是它们都归类于“虚构世界”,及现实生活中无法用五感捕捉到的。
这要看你讲的“现实世界”是广义还是狭义,广义来讲,想象世界也包括在现实中,那就没有“迁移”这个说法了。狭义来讲,我们现在已经处于这种情况了。现实世界就是本我,原始的欲望;虚构(想象)世界就是超我,追求更高层次的东西。许多人在吃饱饭,穿得暖,有地儿住,满足本我的基本欲望后,有了时间和精力发展他们虚构(想象)世界,从而产生更多需求。但是但是,”迁移“这个词会更加偏向于从A地离开,去到B地。而这里的虚构(想象)世界是几乎离不开狭义的现实世界的。就像很少有一个吃不上饭,快饿死的人会思考哲学问题,除非他在之前就已经有完善的精神体系,也就是虚构世界。因此,狭义现实世界很难或者无法和想象世界并排比较,只有当满足了前者,后者才会发展成熟。
最后,必要的尊重肯定是需要的,至于是否要“更”尊重,那就要看你原来比较的具体对象了。
[quote=“hanjiasangeyue, post:19, topic:1211, full:true”]
首先,我觉得现实世界和虚构世界都值得我追求,没有“更值得”这一说法。
我认为可以称作经历。就像主楼里说得,想象出来的东西也会变成我们的记忆,他们和现实中的经历一样,会成为影响甚至塑造我们的东西。不然我们在学习时的思考算什么?
通过想象构造的事件,和现实世界中的经历不同之处在于,如果你没有在现实世界中经历过,那你就无法想象。举个例子,你无法向一位先天盲人解释什么是红色,如果你没品尝过什么是甜味,那你也无法想象一块草莓蛋糕有多么香甜。因此,想象其实是现实经历的一个延伸,或者说想象还是基于现实经历的。
感觉现实经历更真实是因为我们有感官。现实中,我们的经历还由五感组成。我们可以用眼睛观察一个东西,也可以用鼻子闻它的气味,如果它能发出声音,还会被我们的耳朵接收到,甚至某些情况下,我们可以直接用嘴尝它的味道(神农尝百草:D)。这种多感官的刺激,会直接把这些数据传送给我们的大脑。而想象可能只有大脑一个人在“孤军奋战”,想象反馈给大脑的数据还不够多,起码没有现实中用五感来的多。因此可能会产生现实经历比虚构经历更真实的直觉。
我觉得真这样做到了,可能会有点危险哈。根据2.1,这相当于你在虚构世界(或者想象)中产生的“数据”,或者说对大脑的“刺激”,已经等于甚至超过现实中各种感官的总和了。这样或许会导致人们无法有效区分现实和虚构,因为他们似乎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了。所以,或许只有那些因为这个原因,而待在精神院的人,最了解具体情况吧。
命题F下面的问题:
我认为或许不只有命题G里面提到的,想象越详细,越有机会取代现实记忆。F中提到的宗教信徒可能是那些“狂热”崇拜者。他们信奉的宗教很可能把他们从现实中的一些事“解脱”了出来。就像溺水的抓住一根稻草不放一样,宗教,或者所谓的“神迹”是他们最后的希望,哪怕这个希望很渺茫,甚至不存在,他们也会坚信看见了“神迹”。这其实像是“自己说服自己”,“自己欺骗自己”,并非一定是想象干预了记忆。不过命题F中,“感官数据会被写入记忆中,这是不受想象影响的。” 这也不总是对的。就像后面提到,庭审时出现记忆错乱。如果我们的记忆不再清晰,也就意味着能刺激我们大脑的五感减少了,那这个时候,想象能带给大脑的刺激就会大于,甚至远远大于现实记忆。因此这种情况下,我们会倾向于用自己“合理的想象”来替代之前模糊的现实记忆。
这个我认为可以分类讨论:1. 当想象的场景很短(想象持续时间不长)时,一个想象力非常强的人,是很有可能自由将想象世界当作自己真实的记忆。
2. 当想象持续得很久的时候,我们的肉体还是会因为时间的流失而产生反应,这或许会导致身体(现实肉体)和大脑(想象)接收的信息不一样,从而让想象的东西无法像真实的记忆那样符合现实的逻辑。比如,你很饿,然后坐在椅子上想象你吃一顿大餐,吃了一个小时,结束后你起来,还是会感觉饥肠辘辘,甚至有可能还会觉得腰酸背痛,因为你坐着不动太久了。这就是你在“想象”时,现实世界对你造成的影响。
3. 还有一种情况,就是在想象结束后,过了很久,久到你对那时现实状态的记忆都模糊了,那么你想象出来的东西就可能会取代真实的记忆。原因就是之前F里回复的,想象对大脑的刺激>现实对大脑的刺激。
现实是我们能通过五感察觉到的,而虚构则不能。比如,你无法通过观察,知道一个人此时此刻大脑中在想些什么,但你可以通过“虚构世界”中,大脑的推理或猜测,来想象出那人在想啥。所以现实世界只能带来客观的东西,而虚构世界在现实世界的基础上,添加了主观的思想。这也是它们之间的差异。
命题H我也同意,他们是现实世界的产物。
因为自我实现和尊重需求是人们的主观意识,属于虚构世界,并且是因人而异的。那些没有人类进化得复杂的生物,就不会有这种需求,因为他们更加关注于现实世界,却没有那么复杂的虚构(或者精神)世界。它们之所以“在想象中和现实中并没有区别”,是因为现实世界的一部分是虚构世界的折射。
一件事情越接近本我,它在现实中的占比越大。反之,它越接近超我时,就会越接近虚构世界。在这句话的理解中,现实是指:自然发生的事物,和生物的本能反应。这是狭义的”现实“,但其实广义的“现实”是会受到虚构世界的影响的,它是狭义”现实“和虚构世界的共同体和混合体。就像我们的某些行动并不是我们的本能(本我),但是在经过虚构世界(超我)的思考后,我们做出或许将会违背本能的行动,而这个行动就是自我,它像广义现实一样,收到本我和超我两面的影响。
想象食物有多么美味,更加接近超我的概念(虚构世界)。命题H里说得,是“基本的生理欲望”,是能不能吃饱,会不会吃死的问题(更接近本我),而不是更加“高级”的,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吃。因此并不会和命题H矛盾。
认同命题D。问题4中,“我们不再拥有一个客观的历史可以相互验证”,并不会,既然脑机接口中的“类似的现实世界”(或者就叫虚构世界吧),很难在真的“现实”(本我)中验证,那么就在虚构世界(超我)中验证。总的来说,如果命题D中的“现实世界”是广义的现实世界(及 狭义现实和虚构的混合体,或者在命题I中理解为的“自我”),那么命题D仍然正确。我们比如脑机接口中,连接大脑的机器,肯定会保留我们在它创造出来的世界里的“痕迹”和数据,那么以后的人们,就可以用这些数据来作为验证这段历史的证据。
类似,但不完全相同。想象世界纯纯靠大脑构造,而“脑机接口所提供的‘现实世界’ ”是用机械来辅助我们的想象,甚至可以通过刺激我们的五感,来无限模拟出真实世界里的感受。但是它们都归类于“虚构世界”,及现实生活中无法用五感捕捉到的。
这要看你讲的“现实世界”是广义还是狭义,广义来讲,想象世界也包括在现实中,那就没有“迁移”这个说法了。狭义来讲,我们现在已经处于这种情况了。现实世界就是本我,原始的欲望;虚构(想象)世界就是超我,追求更高层次的东西。许多人在吃饱饭,穿得暖,有地儿住,满足本我的基本欲望后,有了时间和精力发展他们虚构(想象)世界,从而产生更多需求。但是但是,”迁移“这个词会更加偏向于从A地离开,去到B地。而这里的虚构(想象)世界是几乎离不开狭义的现实世界的。就像很少有一个吃不上饭,快饿死的人会思考哲学问题,除非他在之前就已经有完善的精神体系,也就是虚构世界。因此,狭义现实世界很难或者无法和想象世界并排比较,只有当满足了前者,后者才会发展成熟。
这就基本回答和解释完了, 现实是不是比起虚构世界更值得追求,如果是,为什么?
最后,必要的尊重肯定是需要的,至于是否要“更”尊重,那就要看你原来比较的具体对象了。